□ 彭忠富
南宋乾道三年(1167年)秋,岳麓山下湘水奔流。一位福建学者携弟子跋涉两千里抵达潭州,岳麓书院山门洞开,千余学子列队相迎。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旷古烁今的“朱张会讲”——一场持续两月有余的学术盛宴,而其主导者,正是时年34岁的岳麓书院主持张栻。
破除门户的学术胸襟
张栻(1133-1180年),字敬夫,号南轩,四川绵竹人。其父张浚为南宋中兴名相,一生力主抗金,遭秦桧排挤贬谪湘粤20余年。张栻生于蜀而长于湘,遵父遗嘱葬父于潭州宁乡。这种特殊的成长经历,造就了他兼容南北的学术视野。张栻幼承庭训,“教以忠孝仁义之实”,后从学于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。胡宏初见即赞叹:“圣门有人,吾道幸矣。”当乾道元年(1165年)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岳麓书院时,张栻以《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》系统提出“成就人才,以传斯道而济斯民”的办学宗旨,彻底破除科举利禄之弊。
尤为难得的是,张栻主动邀请持论相异的朱熹前来辩论。时年37岁的朱熹代表闽学,与湖湘学在“心性论”“工夫论”等核心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。张栻以书院主导者身份正式邀约论敌,首次将书院塑造为超越门户之见的公共辩论平台,此举在当时士林堪称石破天惊。据《岳麓志》记载,张栻为此次会讲精心筹备三月有余,专门修建了可容纳千人的讲经堂。
公开辩论的范式确立
这场会讲持续了两个多月,史载“学徒千余,舆马之众,至饮池水立涸”。
不同于传统的私人论学,此次会讲设有主辩、副辩、记录、司仪等完整架构,面向所有学者开放。据朱熹门人记载,每日与会者除正式学子外,还有大量民间士人甚至贩夫走卒驻足聆听。
此次会讲围绕“中和”“太极”“察识涵养”等核心义理展开深度辩论。在“中和之辩”中,张栻坚持胡宏“先察识后涵养”的主张,认为须先明心体之大本,而后达道之中节;朱熹则主张“先涵养后察识”,强调平日持敬功夫。双方往复辩论数十回合,朱熹后来在答张栻诗中回忆:“始知太极蕴,要妙难名论。”
此次会讲确立了“主讲—问难—辩驳—总结”的完整流程,每日辰时开讲,酉时结束,中间设有三次问难环节。这种规范化辩论模式,为后来的鹅湖之会等学术辩论提供了可操作的范本。值得一提的是,张栻还命弟子将每日辩论要点刻印分发,使未能与会者也能了解进展,这种学术公开化的做法在当时堪称创举。
湖湘精神的熔铸塑造
张栻对湖湘学派的贡献不仅在于学术建设,更在于精神塑造。他先后主持城南书院、岳麓书院、石鼓书院三大基地,使湖湘学派从地域性学术团体跃升为全国性学术力量。
在教学实践中,张栻创立了“经世致用”的教学体系。在岳麓书院,他将课程分为经义、治事、文史三大类,规定生徒必须兼修实事策论。张栻撰写的《孟子说》《论语解》等教材,强调“知行互发”的学习方法,反对空谈性理。这种重实践、讲实用的教学特色,使湖湘学子多能“明体达用”。
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《潭州劝学文》中清晰勾勒出湖湘学统:周敦颐开其源,胡安国父子承其脉,至“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”而大成。值得注意的是,宋人始终将张栻置于朱熹之前,称“张朱二先生”,这正体现了张栻在湖湘学派中的核心地位。宝祐元年(1253年)永州知州虞珵的《永州学释奠诗》更直言:“惟湖湘理学自周元公倡之,五峰、南轩继之”,将朱熹排除在湖湘学统之外,可见当时士林公论。
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形成“一城双星”格局,他首创的“昼夜不息”的论学方式,使湖湘学风呈现出“致知力行”的实践特质。其弟子吴猎、赵方、彭龟年等人后来成为南宋抗金的中流砥柱,正是“传斯道而济斯民”办学理念的生动实践。值得一提的是,张栻在书院中首创“军事策论”课程,亲自讲授边防实务,这种将学术与事功紧密结合的做法,开创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。
学术自由的一座丰碑
“朱张会讲”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。8年后,即1175年,鹅湖之会才在江西上演,而张栻开创的书院辩论传统,最终推动形成了南宋四大书院各领风骚的格局。
元代理学家吴澄在《岳麓书院重修记》中仍坚持“张前朱后”的排序,直至明弘治年间朱张祠建立,才因官学化需要调整次序。但无论称谓如何变化,张栻作为书院公开学术辩论传统的开创者地位从未动摇。明代学者李东阳在《岳麓书院记》中评价:“南轩先生之教,既开湖湘之学统,亦立天下书院之规制。”
800余年后的今天,当我们回首那段在岳麓书院激荡的学术风云,仍能感受到张栻留下的精神遗产:学术唯有在自由辩论中才能创新发展,真理只有在思想碰撞中才能愈辩愈明。可以说,张栻为中国书院制度奠定了最为珍贵的开放传统,他所确立的“和而不同”的辩论精神、“求真务实”的学术态度、“经世致用”的教育理念,至今仍在启迪着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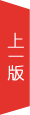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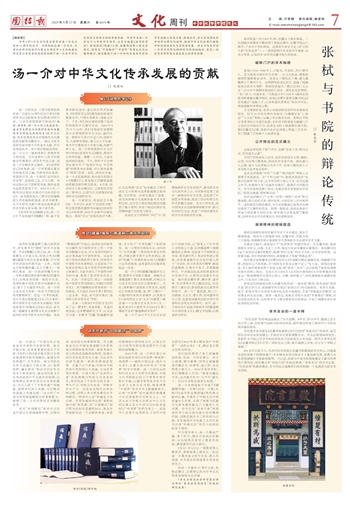

 前一期
前一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