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牛学智
最近,关于文艺批评的讨论又热了起来。特别是青年批评家们,他们思维活跃,勇于尝试新理论、新视角,对文学、影视、网络文艺等各种新形态保持着敏锐触觉,给文艺评论界带来了勃勃生机。这股创新力量,是推动批评话语更新、理解当下复杂文艺现象的重要引擎。
然而,伴随着青年批评的活跃,一些声音也开始浮现:有些评论文章理论高深、术语新奇,却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;有些分析鞭辟入里,却似乎离火热的生活现场和普通人的情感体验隔了一层;还有些讨论,在价值评判的关键点上,显得过于闭环或模糊。这些现象并非个别,它折射出青年批评在快速成长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挑战:如何在保持专业锐度的同时,真正扎根于我们共同生活的这片土地,回应时代和人民深切的文艺需求?
当下中国,社会在深刻变革,文化生态日益多元。手机屏幕成了很多人接触文艺的主窗口,“点赞”“转发”“分享”成了新的参与方式。大众不仅是文艺的消费者,更是创作和传播的重要力量,新的审美趣味、情感表达不断涌现。这种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浪潮,对批评提出了更高要求——它不能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,更需要有连接大众、解读时代的能力。
反观部分青年批评家的批评实践,问题根源或许是多方面的。一方面,现实压力不小。“成名要趁早”的焦虑,叠加学术竞争的压力,有时会让批评实践不自觉地偏向于追求“学术亮点”,比如过度依赖新奇理论、制造生僻概念,把本应深刻的思想交锋简化成了术语的堆砌竞赛。另一方面,面对复杂尖锐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象,有时会倾向于用“学术化”包装避开锋芒,或者因个体成长经历(如独生子女环境、高度竞争的教育背景、消费文化影响)带来的视角局限,难以真正共情更广大群体,特别是基层民众的集体情感和真实生存状态。
这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,一些批评虽然“规范”“精深”,却可能无形中窄化了作品的丰富内涵。比如,对某些备受关注的小说或影视剧的解读,最终可能更着力于搭建精巧的理论模型或个人化的阐释框架,而作品本身所承载的时代气息、社会肌理,特别是普通人的心声,反而被忽略了。这种从“我”出发的视角,有时会削弱批评的公共性,也让描绘出的“文艺图景”与基层文艺现场充满草根力量的生命脉动之间,产生了微妙的距离感。
更值得思考的是,如果这种偏重个体化和学院化的风格,通过学术期刊、评价体系等渠道,无形中成为某种“主流”或“标准”,那么那些真正来自生活一线、带着泥土气息、反映不同群体心声的批评声音,其传播空间就可能被压缩。批评本该是多元声音碰撞的广场,如果格局失衡,其活力和公共价值难免受损。
正是在这个背景下,“新大众文艺”的视野显得格外有意义。它并非要否定创新,也不是简单地怀旧,其核心是呼唤批评回归本源——回归到由无数普通个体,特别是那些常被宏大叙事遮蔽的“无声”大众所构成的“我们”之中。它要求批评穿透过度个人化或学院化的迷雾,重新拥抱共同体的历史命运、集体情感和真实生活。这实际上是为青年批评指出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方向:从“我”的独白走向“我们”的对话。
青年批评的重建,关键在于双脚要重新踏上生活的泥土。这不是要放弃思想的锋芒和理论的深度,恰恰相反,是为思想寻找更丰厚的土壤和更坚实的根基。青年批评者需要勇敢走出理论的“舒适区”,走向广阔的田野:去社区文化活动现场,感受街坊邻居自编自演的活力与温度;听听民间艺人讲述他们的故事,打捞那些被忽略的集体记忆;更要重视普通观众、读者的真实反馈,那里藏着最质朴也最有力的审美体验和价值诉求。只有在生活的现场,批评才能感知到时代最深沉的律动。
要让这种转向成为可能,需要内外合力。其一,评价体系需更包容。在鼓励理论创新的同时,也要认可那些扎根现实、富有社会关怀、能有效沟通文艺与大众的批评实践的价值。不能只看论文发在哪里,更要看它回应了什么现实问题。其二,平台渠道要拓宽。报纸、网络、新媒体等平台,应有意识地搭建桥梁,为来自不同背景、反映不同群体视角的批评声音提供舞台,让广场真正“众声喧哗”。其三,实践机会应增多。高校、研究机构可以多组织青年批评者深入基层,参与文艺实践,进行田野调查,帮助弥合书本与现实的距离。其四,自身视野待拓展。青年批评者自身需保持警醒,主动突破个体经验的局限,培养更深厚的历史感、社会感和人民情怀,让精研的理论与广阔的社会现实对话融合。
青年批评的活力是其宝贵财富,当这份活力与回归生活本源的自觉相结合,青年批评才能真正成为连接文艺创作、社会脉动与人民心灵的坚实桥梁。期待青年批评家们俯下身,用心倾听那来自大地深处、沉默却无比磅礴的轰鸣——那是时代的心跳,是人民的心声。只有听见这声音,青年批评才能在时代的洪流中,淬炼出真正有力、真正属于人民,也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“真声”。这声音,终将汇入时代壮阔的合唱,为文艺的百花园注入持久而深沉的生命力。
(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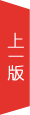



 前一期
前一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