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陈 蓉
节气到了寒露,风便成了街巷里最勤快的信差。它穿过老槐树日渐稀疏的枝丫,把那股清冽的、带着霜意的消息,挨家挨户地传递。
巷口王师傅的修车摊子,总是清晨第一个感知到这讯息的。他放下那把被机油浸得发亮的扳手,朝着掌心呵出一团白气,随即不慌不忙地从三轮车座下掏出一双洗得发白的旧棉手套,稳稳地套上。这便是寒露的头一桩暖事——它让你懂得,抵御世间风霜的,未必是轰轰烈烈的烈焰,往往就是这一针一线织就的、贴肤的安稳。
街对面,李婶的包子铺正笼罩在一片磅礴的白雾里。那蒸汽比夏日里更浓稠、更有底气,一团团涌出来,在冷空气中久久不散,仿佛给这清寒的早晨筑起了一道暖和的堡垒。排队的人们也缩着脖子,跺着脚,却不见焦躁。只等那笼盖一掀,一股更扎实的热浪混着面与肉的醇香扑面而来,一口咬下去,满嘴的暄软与鲜香,仿佛把一团被驯服的、温存的日光咽进了肚里。这又是寒露的一桩暖事——它让最寻常的烟火吃食,成了此刻最叫人眷恋的、近乎于救赎的恩物。
我们这条老巷,平日里大家各自奔忙,门扉虚掩。可节气一到,邻里间那层看不见的薄冰,便好似被这寒露之气给“咯噔”一下打破了。午后,阳光斜斜地照过来,落在谁家门前空着的藤椅上。二楼的陈奶奶便开始忙活了,她晾晒的不只是一床床新弹的棉被,还有一簸箕的萝卜干。那萝卜干切得细细的,摊在竹篾上,吸饱了日头,泛着一种暖洋洋、金灿灿的光泽。路过的人总要驻足,夸一句:“陈奶奶,您这萝卜干晒得可真俊!”老太太便会笑得满脸褶子都舒展开,硬要抓一把给你尝尝。那萝卜干嚼在嘴里,韧韧的,甜中带咸,满是阳光的味道。
隔壁单元的赵老师,则把他那些宝贝兰花一盆盆地搬出来,让它们也享用这“秋阳之礼”。他一边用软布细细擦拭叶片,一边和旁观的王师傅探讨着“春化”的道理,说这寒露时节的凉,恰是来年开花的关键。我是不大懂这些的,但我爱看那墨绿的叶片在澄澈的秋光里,泛着沉静的、油亮的光。那光景,让人觉得岁月静好,不过如此。
黄昏来得急促,这时家家窗口透出的灯光,便成了寒露之夜最动人的暖事。你走在巷子里,能听见隐约的炒菜声,能闻到各色饭菜的香气交织在清冷的空气里。不知哪家窗口,飘出咿咿呀呀的戏曲声,腔调拖得老长,在巷子里悠悠地转着,非但不觉得吵,反倒给这静谧的夜平添了几分生气。
回到家中,我拧亮书桌上那盏台灯。光晕如水,洒在桌案一圈,人的心便也沉静下来。寒露之夜,正宜读些闲散的文字,或与家人围坐闲话。手边一杯新沏的热茶,茶叶在杯中舒卷沉浮,袅袅的气体曲折上升。窗外,风声渐紧,偶尔传来枯叶擦过地面的“沙沙”声,清晰而遥远。但这屋内的暖,是实实在在的,它被四壁妥帖地护着,被这盏灯温柔地照着。
我忽然觉得,寒露这个节气,骨子里是慈悲的。它并非一味地施予严寒,而是用它清冷的手,为我们从这庞杂的人间,细细揩拭出那些平日里被忽略的暖意来——是那双旧手套,是那个热包子,是邻人馈赠的一把萝卜干,是窗口的一盏灯,是杯中一缕茶烟。它们微小如尘,散落在生活的缝隙里,却在这寒凉的时节,汇聚成足以慰藉一生的光与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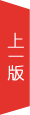



 前一期
前一期